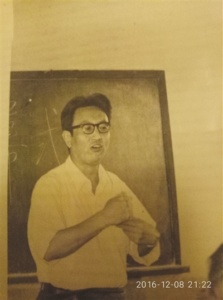下班已经很晚了,从旧金山坐上火车往家赶。刚到家,突然看到微信上传来一条噩耗,我在南京的三姨爹走了。
三姨爹郁慕镛是上海人,五十年代北京大学毕业,此后一直在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直到退休。他是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我的印象里,三姨爹个子高大,一表人才,是典型的五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有学问、有理想、善良、正直。“文革”期间,即便他学富五车,但也和当时其他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样,被打入“臭老九”一类。当时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不如工人老大哥,是被改造的对象。当时,他和我在南京的姑姑(我父亲的亲妹妹)都是有理想的知识青年,他们因共同的理想而相识。我姑姑在“文革”中曾一度是南京市里的风云人物。其实当时我姨爹一直是欣赏并追求我姑姑的。但我姑姑却始终对这个有学问,相貌英俊的姨爹不感冒。我姑姑当时是一心想在政治上向上,想有所作为。可是这个解放前上海资本家出身的姨爹是不可能帮助她的,可能反而会拖她的后腿。再加上她自己本身也不是根红苗正。她的父亲我的爷爷,曾是国民党少将、国民党九十军军长。所以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下,我姑姑和姨爹是注定不能结合在一起的。
命运就是这么神奇。众里寻她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姨爹虽然追求我姑姑未果,却通过我姑姑认识了我三姨。

我的三姨年轻时命苦。小时候家里很穷,她很小就出来工作了。每月领了工资后她就寄钱给她在大学读书的二姐(也就是我妈),还要赡养父亲。后来结婚生孩子。很不幸,孩子生下来就死了。没过几年,丈夫也生病去世。我三姨当时的处境引起了当时还是单身的姨爹的同情。他表示愿意与我三姨谈朋友。我姑姑就给他们作了介绍。后来他们真还谈成了。不久结婚,还有了孩子。我姨虽然没什么学问,但很会过日子,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我姨爹从内心里感到很满意,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
我记得小时侯,暑假时,我三姨总是要接我和弟弟去她家住一段时间。有时她要上夜班,这时姨爹总是会照顾我和弟弟吃饭睡觉。他还辅导我和弟弟的暑假作业,带我们去书店买小人书,星期天他还带我和弟弟去南京玄武湖划船游玩。他像三姨一样,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

我后来在大学期间,有一阵对人生时时流露出消极的想法,特别是我父亲病重以后。姨爹知道后,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我,开导我要树立正确乐观的人生观。加上我三姨也常常写信鼓励我。现在想想,他们当时给我写的信以及鼓励开导,对帮助我走出当时的消极处境起了很大的作用。再后来我大学毕业分到南京工作,这中间姨爹也帮了不少忙。当时湘潭大学毕业分配是没有名额在南京的。我姨爹找到了他的学生引荐了我,想办法把我分到了南京,让我能够跟亲人呆在一个城市照顾他们。
还记得我父亲在南京病重期间,三姨爹一个人忙里忙外又帮了不少忙,又是跑医院找血源,又是跑图书馆找资料。当那天接到父亲的病危通知书,我不顾一切从湘潭上了火车,36个小时的车程,一路哭过来,等到了南京已经是大半夜。举目无亲,环顾无人之际,忽然发现三姨爹一个人在火车站出口处等着我。顿时我倍感温暖。
中国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得到重用。三姨爹焕发了学术青春,在教学科研和培养人才的事业上蒸蒸日上,并取得了卓越成就,其科研著作在海内外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姨爹在经济条件上也大为改观。但他对我三姨的感情依然一如既往。虽然他们在学术领域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但他们知道彼此都无法互相离开那长久建立起来的亲情和温馨的家庭。
愿三姨爹一路走好。天堂里没有病痛折磨,可以在那里得到永远安息。
(责任编辑:陈鹤鸣)